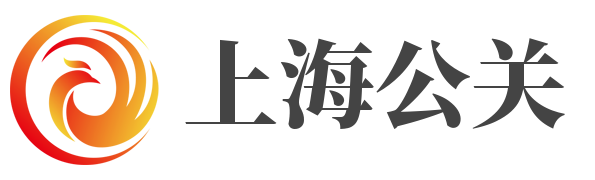参加了玫瑰碗大游行
?002年面世,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人性化机器人。ASIMO周游世界各地,成了著名“人物”,在瑞士爬过坡,参加了玫瑰碗大游行,还在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与好莱坞名流交往。你可能以为,ASIMO是某个硅谷创业公司里的一群博士在好奇心驱使下设计出来的产品。但事实上,却是本田汽车公司的下属部门——本田研究院(HRI)发明出来的。本田在美国、日本和欧洲都设有基地和办事机构。为什么一家汽车公司会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中来?而这件事又与需求有什么关系?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:我们总认为本田是一家汽车公司,但本田其实是一家发动机公司。从割草机到超轻型飞机,为各种产品提供发动机。本田的过去,主要依存于长达一个世纪历史的摩托车和汽车行业,但公司的未来(和所有公司一样)却尚未成型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田会进入机器人领域。利用这种探索新兴技术的方法,来寻找并培养下一个大型产业。从中,本田希望能创造出大规模的新需求。本田的工程师在公司对移动性强烈兴趣的驱动之下,于1986年决定创造出一款行走机器人,来模仿人类运动的复杂性。他们去到动物园,观察各种动物的行走方式;他们研究甲虫腿的结构和功能,并将其与人类四肢的关节进行对比。本田的第一个完整的人性化机器人P1,有着美国国家橄榄球队队员的身型——身高188厘米,体重179公斤。重量中的大部分是因为一个内置式背包,其中装有各种线路和一个大电池。随后推出的机器人类型,则越来越娇小优雅。作为机器人之王的ASIMO本身,则仅有高129厘米,重量仅为54公斤,可以用每小时5.95里的速度行走。如今,全世界约有100个ASIMO机器人,在各类研究机构中发挥着自身的性能。同时,他还是本田公司的形象大使。在本田公司的文化中,基础研究有着深厚的根基。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曾说过,“研究与开发的真正价值,存在于对陌生领域的探索。”纵观本田发展史,我们就会发现,每一位CEO都来自于公司的研发部门。譬如,本田现任总裁兼CEO尹东孝绅还兼任研发部总监,最初被吸引来到本田工作,就是因为公司雄心勃勃的航空和机器人研究。如今,本田研究院将重点放在对各类技术挑战的开放式探索上,其明确的目标就是“为社会做贡献”。公司招聘行业顶尖的研究人员,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资源,让他们进行自己手中的项目,即使这些项目对公司目前的产品线或利润表并无直接价值。在本田研究院,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未来。HRI的开放式研究工作通过高产水稻基因、强力燃料电池,以及超轻机身商用飞机设计(由比铝材料还轻的合成塑料制成)等各方面的创新,为本田公司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机会。本田甚至还被提名为俄亥俄州最大的有机大豆生产商。当初本田进入这一领域,主要是为了在将汽车从日本运抵美国之后,用大豆填满集装箱,而不用让货轮空驶。后来,本田公司在大豆生产的基础上,又开始销售发酵大豆,以帮助人们溶解血栓。从这些例子中,我们可以看出,基础研究并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。科学家通常会在寻找A的过程中发现B,而其间又在C上取得突破。这样的发展,既实现了社会效益,又提高了公司利润。在研究如何阻止牛奶传播疾病的过程中,路易斯·巴斯德发展出了免疫系统理论以及疫苗技术,这也是曲折上升发展模式的一个案例。同样,ASIMO用于监测并控制机器人运动的系统,也产出了其他的技术,现在正用于开发本田的行走辅助设备,帮助提高年老体弱或残疾人的移动能力。这些技术包括臀部/腿部的板状结构,对枴杖发出的信号予以回应,并提供需要的支持。只要数一数年纪在75岁以上的人数,你就能开始感觉到这一技术的巨大前景。ASIMO还激发出了DiGORO机器人的发明。这款机器人能通过头部的摄像机模仿人类的运动,并学会如何打扫卫生,保持房间清洁。回到汽车行业,ASIMO技术还发展出了日产的车道保持辅助系统,利用摄像机和方向盘控制来避免汽车偏离车道。如此看来,ASIMO和其他HRI下属的项目,都具有解决客户麻烦和人类问题的全球性潜力,并能为日产开发出一系列巨大的21世纪新需求。本田这家跨国公司在基础科学上进行投入,让我们又看到了昔日贝尔实验室和RCA实验室的光辉。但这并不是21世纪唯一有效的发现与创新模式。而第二类模式,就是著名的MIT媒体实验室展示出来的“demo or die”研究模式。媒体实验室是一片乱中有序的景象,从这座闪闪发光的玻璃大楼里可以看见几百个研究项目在各自发展。当你走进大楼,身边就会不时有人骑着“绿轮子”(GreenWheel)从你身边飞驰而过。这是一款电动自行车,在轮轴处加装了集成电动发动机和电池,可以翻山越岭,比普通电动自行车能行驶更长的距离,也让很多一般不会考虑骑自行车的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交通方式。旁边几个学生正在CityCar样车的巨幅照片下面,摆弄着一辆叫作Robo的小轮车折叠电动摩托车。这种车型专门为交通繁忙的城市地区设计,供人们搭车之用。这些车辆是为了满足“按需移动”(Mobility on Demand)这种新型使用模式的需求。在这种模式之下,电动车辆被放置在遍布全城的充电站中。用户只要走到最近的充电站,刷一下门卡,就能驾驶着电动车辆出行,然后在任何一家充电站归还。博士生莱恩·秦(Ryan Chin)解释道:我们为了应对如今各大城市极端密集的交通状况,而设计了各种类型的城市移动设备。主要问题是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的问题。从家到火车站,或者从火车站到达目的地,就是这样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自己驾驶,因为使用公共交通太过不便,缺乏灵活性。但‘按需移动’系统则会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据已故MIT建筑规划学院院长兼媒体实验室智能城市研究项目组组长威廉·米切尔(William Mitchell)所言,这样的创新途径是整体性的,而CitiCar则代表了四种主要思想的汇合:交通工具从内燃机向电力驱动的变革;利用互联网处理海量数据;将交通工具与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相集成;以及利用动态定价的电力、公路空间、停车场位以及共享用车的实时系统的创造。如此高质量的远大理想,是需求创造者才有能力玩的游戏。这正是媒体实验室的标志。每一家优秀的实验室都有别具一格的文化。在媒体实验室崭新的玻璃大楼中,研究人员投身于各类项目,包括汽车、机器人、生物机电手臂、高精尖仪器,以及早期教育项目。这些项目之间彼此透明,可以形成互动——是一种利用学科重叠来强化实验室多学科特性的“鱼鳞模式”。实验室规模相对较小,运营预算约为3500万美元,为40名左右的教师、高级研究员、访问学者和大约10名研究生提供支持。从这样的规模看来,实验室的产出就显得非常庞大,覆盖面也非常之广。在25年间,从实验室诞生的创业公司超过了80家。举例来说,从实验室脱离出来的电子墨水技术,就是电子阅读器显示清晰而耗电低的关键。“让每个孩子用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”(One Laptop per Child)也是媒体实验室分拆出来的公司,由此激发出了ASUSTeK的Eee上网本灵感。另一家公司感知网络(Sense Networks),利用手机数据制作真实世界的地图,十分类似于谷歌做的互联网索引。Harmonix(“摇滚乐队”视频游戏背后的音乐技术)以及TagSense(RFID和无线传感)也来自于这家实验室。实验室还与业内伙伴共同开发出了其他产品和项目,包括为IBM开发的用来进行大规模文本分析的WebFountain,以及为北电开发的无线筛分网络。上述的这些创新中,会有一些成为大型新产业的基础,并创造出成百上千万的工作机会吗?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,但是媒体实验室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前进。实验室2005年至2011年的主任弗兰克·莫斯(Frank Moss)说道:媒体实验室正在关注即将在未来10年内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。无论研究项目本身被称为科学还是工程,